09年福建一面包车被拦,警方发现车内有奶粉,调查后车主被判死刑这三大星座,才是最适合恋爱的人选
“货到手了?”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,在福建省安溪县,一个男人正在低声问着旁边的中年妇女。
“到了!这次的货有点不安份,记得用点药,小心点!”
“知道。对了,不该问的别问。”
中年男人接过货,仔细将其放进后备箱,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货。
为了拿到货源,所有人都分工明确,有人去找货,有人找买家,还有人负责牵线运输。
而中年男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。
在他的上面需要接应找货的女人;在他的下面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“媒婆”,“媒婆”们找到买家,再由中年男人将货运输过去。
每个人都只用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,然后根据分工不同抽取提成,除了中年男人,大家都知道得很少,就是害怕走漏消息。
现在,中年男人带着满满一车货驶向未知的远方,这车货于他是金钱,于别人便是家破人亡,痛不欲生……

走上歹路
安溪人李地基没读过什么书,五十岁一过,李地基明显感觉自己身体机能下降,靠着一辆破旧面包车干起了运输的活计。
可是只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司机,不仅累还很难受到别人的尊重,挣钱也少得可伶。
再加上,李地基年轻时常年奔波在外,和唯一的儿子并不熟悉,儿子长大后,两人也总是吵架。
因此,李地基希望多挣点钱这样就能在儿子面前有话语权,也能多帮衬一下儿子的生活。
于是,在李地基56岁这年,他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果断走上一条犯罪道路。
当时李地基拉了一个客人,客人随口抱怨最近的人贩子真是猖獗,大街上都敢抢孩子,随后再把孩子高价卖出赚些黑心钱。
客人对人贩子愤愤不平,李地基却是起了歹念,既然拐卖一个孩子如此容易,自己可不可以试试呢?
在李地基仅有的文化水平里,从不觉得拐卖孩子是在违法犯罪,他只知道既然别人可以干,自己为什么不能干?
他自己的儿子是儿子,别人的孩子却是商品,是一个价值几万块的“货物”。
由于李地基常年跑车,十分熟悉安溪县的各个车站和周边农村,再加上跑车认识不少人,李地基心里也有了合适人选。
他知道买卖儿童这件事,光靠自己一个人肯定做不了,他需要找一些帮手。
于是李地基先后找到陈莲香、吴秋月吴随清姐妹、彩霞、谢旦等人,他们俨然组成一个运转精密的组织。
各自负责其中一环,再由李地基串联起所有人,让拐卖儿童这件事高效进行。
陈莲香是李地基认识的人贩子之一,也是整个团体中最冷血的,她的残忍来源于无知,明明是一个快六十岁的人,却有着最纯粹的恶。
光看脸,你或许会觉得陈莲香是一个慈祥的女人,她身材偏向圆润,也总是喜欢笑脸相迎。

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见了她都不会有什么戒心,而她正是靠着自己的外貌实施拐卖。
她趁大人不注意,或是一个转身,或是接了一个电话,就在这眨眼之间陈莲香抱起孩子就跑。
当然她也会给孩子一点小玩意,哄着孩子不要哭闹。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好骗,但经验老道的陈莲香可不怕。
孩子哭闹就用暴力解决,直接把孩子迷晕后快速抱上车,父母想追也追不上。
很快,疯狂残忍的陈莲香就拐卖了数十个孩子。
哪怕已经被警察抓捕归案了,在法庭上陈莲香还是没有丝毫悔改。别人问他抢走孩子,破坏一个家庭你不会愧疚吗?
陈莲香眼皮都没抬一下,无所谓地说道:“她们又不是不能生,孩子没了,再生一个不就好了。”
短短一句话,震惊在座所有人。一个人最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,陈莲香简直不配称之为人。
而警察在给陈莲香录口供的时候,更是多次见识陈莲香的无知和残忍。
警察问到其中一个被她拐卖的孩子去到了哪里?
陈莲香淡淡答道:“那孩子一直在哭闹,实在太吵了,我害怕孩子的哭声把警察引来,就把他扔到河里去了。”
陈莲香不明白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,更不知道人命的可贵,所以坏起来也是干脆。
更可怕的是,哪怕她坏事做尽,她都没有展露出丝毫后悔,实在令人不寒而栗。
不仅如此,为了挣钱,陈莲香会专门物色年龄更小的孩子,最好不要超过三岁。
这样的孩子,买家买回去带个几年孩子什么都记不得。
要是比较大的孩子或许会记得亲生父母,总是想着逃跑,至于孩子逃跑后会遭受怎样的对待,陈莲香从不操心这些。
当然,李地基本人也比陈莲香好不到哪去。

被捕归案
陈莲香拐卖来的孩子都给了李地基,然后李地基再根据孩子的“质量”给陈莲香分成,一般都是几千元不等。
随后,由李地基把孩子送到安溪周围的农村,其实李地基的买家几乎全是农村人。
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的儿子,但是看到周围许多人都买了儿子,于是跟风在李地基那里下了单。
还有的买家,则是因为儿子大了之后独自在外居住,父母一个人嫌寂寞,就想再买一个儿子回来养着。
反正养儿防老,这些老人从不闲自己的儿子多,只害怕老了都无人送终。
当然要找到这么多买家,就不是李地基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了。
李地基还需要牵线搭桥的人,也就是谢旦、吴秋月吴随清姐妹以及彩霞等人。

谢旦和最初的李地基一样都是一个只会靠劳作赚钱的老实人,李地基先是找到谢旦,用金钱利诱他帮自己在村子里找买家。
一开始谢旦还不愿意,害怕这件事有风险,但无奈李地基给的钱太多,谢旦很快就妥协了。
大家可能会好奇一个孩子究竟卖了多少钱才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。
其实李地基一个孩子也就卖到三至五万不等,这连一个人能创造的财富的零头都不到。
可在李地基手里,三五万就能彻底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和命运。
而李地基贩卖一个孩子可以抽取五六千元,其他人再抽取一部分。
为了让李地基等人行动方便,团队里还有专门提供食宿的人,给李地基他们找好安全的下脚地,再准备好足够食物,以应对突发状况。
平常都没有冒出过的机灵劲,一到了犯罪头上,脑子都灵光了起来。也真是讽刺!
谢旦在村里联系买家,吴秋月姐妹俩也是买家联络人之一。

吴秋月一直都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,自她嫁到邻村去后,懒惰的本性更是发挥到极致。
她三天两头就往镇上跑,家里的农活从来没做过,就连打扫屋子都是靠心情。
镇子上才是吴秋月的家,真正的家反而成了宾馆。
吴秋月的做派她的丈夫自然忍不了,两个人天天都要吵。
而吴秋月也不是个好说话的,拿起锄头等农具就和丈夫对打,简直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笑话。
一直到吴秋月生下孩子后,她还是不见收敛,哪怕二儿子患上了小儿麻痹症,她内心难得的母性也没能被唤醒。
继续在外逍遥快活,也继续和丈夫生孩子,一连又生了好几个。照吴秋月这种花钱不挣钱的活法,自然日日都是资金紧缺。
所以当李地基找到她的时候,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
由于吴秋月只是牵线搭桥,她的分成会少一点,也只有几百块钱的样子。

吴秋月有了这个赚钱途径后,又拉来了自己的姐妹吴随清。
吴随清的丈夫不久前去世了,三个孩子全靠她一个女人养,再努力也还是养得艰难。
有了快速挣钱的方法,哪怕是歪门邪道,吴随清还是参与了。
于是,一个分工明确的拐卖组织就悄悄诞生了,他们藏在黑暗里,挣这世上最肮脏的钱。
可偏偏团队里的人大多是文盲,他们要么心硬如铁,要么从一开始就不觉得自己错了。
全都拿着钱满足自己的私欲,内心没有片刻愧疚、后悔。
一直到警察宣读法律条案、把明晃晃的罪证摆在众人眼前,还是有好些人不觉得自己错了!
一天夜里,李地基和以前一样载着装有孩子的面包车往买家家里赶。
半路休息的时候警察突然来了,原来是因为李地基的面包车没有车牌。
李地基一看警察来了,立即叫同行的女人抱着孩子出去,装作不认识的模样,自己留在车里。

警察来到车周围,让李地基下车解释为什么没车牌,看见面包车里有许多奶粉和尿布的时候,内心已隐隐警觉。
警察询问李地基为什么拿走车子的车牌,李地基避而不答,只强调自己是本地人。
可警察看车里也没什么赃物和大规额现金,一时之间也没反应过来。
此时,一个警察看着奶粉,突然想到了刚刚那个抱着孩子神色慌张的妇女,心中警铃大作,立即去追那个女人,同时把李地基带回警察局。
哪怕李地基已经到了警局,他还是在嘴硬。
还是警察从李地基的手机里发现了端倪,其中几句“货很漂亮”、“货没问题”之类的言论立即引起警方注意。
再翻看李地基手机的联系人,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有,大多都是农村的,其中还包括西双版纳等地。
于是,警察立即将李地基判为拐卖嫌疑人,对其进行盘问。顺着李地基的名单,追查到其他几个人,以及几十个被拐卖的孩子。

法院审判
人赃俱获后,陈莲香、李地基等人站上了安溪县法院,接受一审。
由于案件牵连甚广,光是卷宗就写了几十本,判决书更是上百页。
同时,那一天来旁听的人坐满整个法庭,其中大多都是拐卖中的受害者。
虽然,如今被拐的孩子大多已经找回,但是他们还想看到罪犯伏法,失子之痛才能有些许安慰。
几个人站在法官面前全都低下了头,只有李地基始终高昂着头注视着法官,神情间不见后悔更没有丝毫愧疚、敬畏。
明明心无悔意,可面对法官提问时又开始推脱刑责。
说自己只是个中间人,只负责运输孩子其他一概不知。
同时,他还把一切罪责都归咎到“彩霞”身上,由于当时彩霞还潜逃在外,警察没有她的口供。

因此李地基就想把罪责一溜烟都赖到彩霞身上,以为这样就可以洗脱自己的罪责。
李地基说自己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,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个司机,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,每次只负责运输,也就挣个几百块钱。
见李地基开始抵死不认,其他几人也照葫芦画瓢,纷纷开始推脱。
吴秋月也说自己只是帮那些想要儿子的家庭联系了一下,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甚至当庭耍起无赖,不会回答的问题全都说我不知道。
法官也有点生气,直接质问道: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,是如何在山洞中存活八个月的?”
当时吴秋月为了躲避警察逮捕,直接跑到山上躲了起来,这一藏就是八个月。
警察搜山之后才找到她,当时吴秋月藏身的山洞里还剩下不少食物和水。
吴秋月听见法官的提问,害怕会牵连到自家丈夫,又开始一口把罪责担下。

说水和食物都是自己找的,丈夫只上来看过她几次。但事实却是在吴秋月害怕的时候,丈夫还会上山陪她过夜。
一群罪犯,死到临头才开始祈求诸天神佛,希望可以放自己一马。
可若是求神拜佛有用,就不需要警察了,最后几人的审判如下:
李地基、吴随清2人被判处死刑;吴秋月、谢旦2人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;吴秋月的丈夫郑万年以“窝藏罪”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还有一系列买家视情节轻重进行了判刑。
听到自己即将死亡,李地基的内心终于有了波动,他看向坐在后面的儿子,一时也是相顾无言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哪怕到最后,这一伙人中还有许多人不觉得自己错了,他们只说自己不该违法,或是嘟囔不知道这件事是违法的!
可法律明明是最低标准,难道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每一件事,都是可以做的吗?
推荐资讯
- 想知道那些微商的货源都是哪里弄来的?2024-01-01
- 微商怎么找货源??2024-01-01
- 微商如何找一手货源?分享4种个人经验方法2024-01-01
- 奔走相告(不管你做的有多好别人还是说你不好)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上班就认真工作,不管你做不做电商,这36个货源网,你必须得知道!,2024-05-06
- 这都可以?(货源除了1688还有什么网站)货源除了1688还有什么网站可以卖,除了1688以外,这5大货源网站你必须要知道!,2024-05-06
- 深度揭秘(无货源网店在哪里开)无货源网店怎么赚钱,想做无货源网店可以去哪里找货源,求带?,2024-05-06
- 不看后悔(除了1688,新手淘宝还要知道的10个货源网站是什么)除了1688,新手淘宝还要知道的10个货源网站,除了1688,新手淘宝还要知道的10个货源网站!,2024-05-06
- 不要告诉别人(货源网站排行榜前十名)有什么好的货源网站,你不会还不知道最全的50个!优质货源网站叭叭叭叭~,2024-05-06
- 奔走相告(批发网除了1688还有哪些平台好)批发除了1688还有哪里可以批发,批发网除了1688还有没有更加好的货源网站?主要想批发女装,男装,童装,还有童鞋子这一类的。?,2024-05-06
- 这样也行?(一件代发货源网站大全)一件代发货源哪里的可靠,一件代发货源哪里找比较可靠?,2024-05-06
资讯动态项目推荐
- 知识指南
- 经营技巧
- 知识营销
- 苹果走货速度加快:果农货交易5月15日显著提升泰山封禅帝王:秦始皇实至名归,宋真宗是来“打酱油”
- 苹果走货速度加快:果农货交易5月15日显著提升世界第一个电话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?年轻人还不知道吧?
- 供给足需求旺!"五一"假期临沂居民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溥仪登基时,他的父亲摄政王说了三个字,结果三年后清朝灭亡了!
- 苹果市场到货增多:下游走货不快,五一节销售行情平平一60多岁老人坚称自己是溥仪儿子,还拿出了证据,专家哭笑不得
- 苹果市场到货增多:下游走货不快,五一节销售行情平平原创一支射出的箭有多大威力,能射死人吗?赵云、李广、赵匡胤最清楚
- 鸡蛋价格小幅回升但供需宽松或维持低位滨鹬连飞5天5夜后,在渤海湾大吃1周,再飞3天赶往北极繁殖
- 苹果市场到货增多:下游走货不快,五一节销售行情平平为何说“原子弹下无冤魂”?你看战时的日本女人在做什么,并不冤
- 供给足需求旺!"五一"假期临沂居民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夷陵之战损失不过5万人,为何却说蜀国一蹶不振?原因你想不到
- 苹果市场到货增多:下游走货不快,五一节销售行情平平皇太极去世后,其长子已34岁,为何年仅6岁的顺治继
- 供给足需求旺!"五一"假期临沂居民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活在李世民阴影下的李建成,到底是个怎样的人?别被影视剧骗了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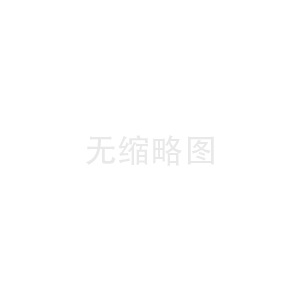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我要入驻(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)
已有 1826 商家通过我们找到了合作客户